子产、叔向、晏婴三人分属三国,他们各自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,而在春秋时期的舞台上纵横。正是他们三人的功业,使得当时弱小的国家有所依靠,因为战争杀伐减少,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因此说他们三人是当时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也不为过。
三人同为执政大夫,皆属士族出身,其中叔向与子产为其国同姓卿大夫,而晏婴则为齐国的异姓卿大夫,这其中微妙的身份区别,致使他们对于国家有不同的态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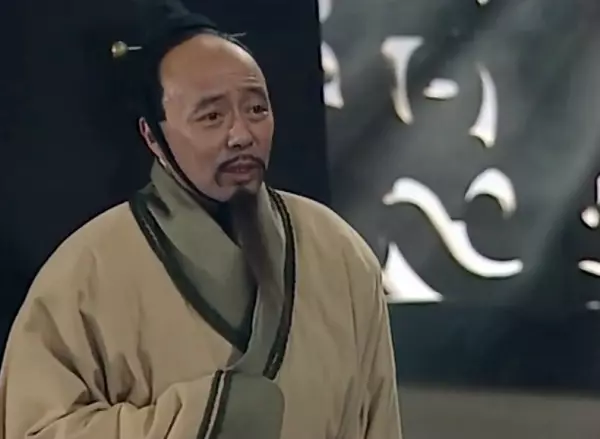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晏婴剧照
纵观春秋时期,执政大夫事君谋国,莫胜于子产,其为人,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说道:“有君子之道四焉;其行己也恭,其事上也敬,其养民也惠,其使民也义。”子产于鲁襄公十九年为卿,从政之初,正逢晋楚争霸最激烈的时期。宋国、郑国两国处于两强势力交界之处,形同两强俎上肉。
因此,以郑国之弱势,当强横之晋、楚,晋国胜则归晋,楚国霸则从楚,疲于奔命。对外,已经十分不易,然而对内,则更是为难。郑国公族“七穆”骄横,子产一系不过是弱族而已。由鲁襄公十年至三十年,这二十年间,各家族间互相倾轧、斗争激烈,当时子产已经为卿,然而他施政全力对外,对公族之间的是非,毫不过问。
子产对外功业彪炳,鲁襄公二十二年对晋国征朝、二十四年寓书劝晋国范宣子轻币、二十五年以入陈之功献捷于郑、二十六年主张不御楚寇等等,以贤达著名于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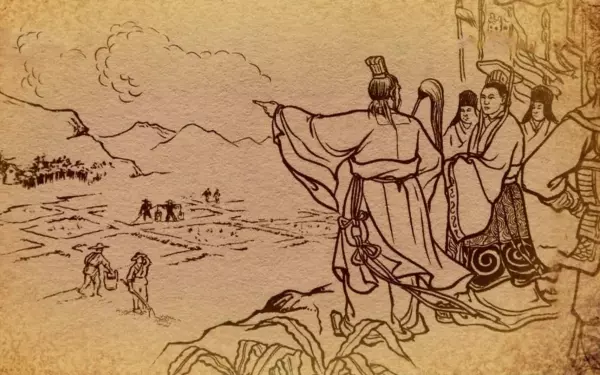
子产治国
所以子罕以子产之贤,将执政的位置让与子产,子产既握有权柄,遂将全部精力投入重建郑国中来。
子产执政后的政绩有:
一、运用政治手腕,安定强族,讨平国内骄横之公族,以辅国人。
二、从事四大建设:都鄙有章、上下有服、田有封洫、庐井有伍。
三、作丘赋、增加赋税,充实军备。
四、铸刑书,以法治代替礼治。
子产从政一年,内政以修,外患以平,国家晏然称治,诚为当时政坛上有担当的一位执政大夫。
叔向是晋国的外交家,又是晋平公傅,在晋国享有很高的地位。由于晋国为当时的霸主,许多记载叔向的资料,都是关于外交场合之中的言论,很难具体地交代他的从政成绩。不过,如果将其言行与子产、晏婴相比较,他应该是当时保守派势力的代表,也是以礼著称。
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晏婴剧照
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,晏婴、叔向、子产,毋庸置疑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我们注意到,晏婴、叔向、子产都是以坚持礼制的态度,来维持其既有权势的保有,为了对抗外在政治环境的不断变迁,他们将礼制视为不可动摇的根基。
事实上,对于晏婴、叔向、子产三人而言,礼是无处不在的。在外交会面的场合、祭祀的场合、丧葬的仪式、政治上的封赏甚至于安定政局,都是礼的范围。
郑人铸刑书,这是礼制的崩坏。在这一年,叔向给子产写了一封信。我们都知道,铸刑书是时代之趋势,避无可避的,而子产只是高瞻远瞩地先行预知了这个未来的趋势,所以就公布了刑书,也引起维护传统礼制者的一片讨伐之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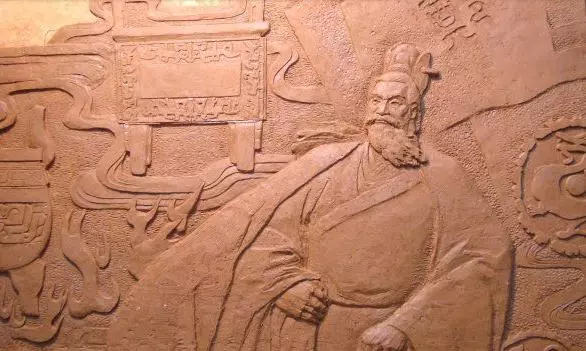
子产铸刑书
子产难道不晓得会因此受到支持礼制者的谴责吗?关乎子产对叔向的回应,可以明显地看到子产在做这个决定时,已经知道抛弃他过去的“习惯做法”,必然会引起属于礼治一派的非难,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做了这样的决定,这是为什么?
子产其实有不得不实行法治的苦衷,在当时还没有铸刑书之前,并没有明确的惩处方式来规范那些犯了罪的人,子产在治理国家时注意到了郑国的各项问题,礼已经不足以解决这样的情形,所以子产选择了法治。
对于叔向而言,子产背弃礼治的行为,他是完全无法谅解的。礼对于叔向来说就是:“政之兴”,礼贯通了所有政治问题,并且可以解决任何的政治争端。由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叔向的记载看来,要叔向认知礼无法含括现实人生所遭遇的全部问题,是很难的。
史书中的叔向,就人品而论,既不贪也不狠,也不奸诈,他勇于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表达出来,以至于连季札都劝他要少讲话,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,这样的人必定对自己认定的事实相当坚持。

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晏婴剧照
子产、叔向同属公族出身,国家兴亡,如同家室兴衰,彼此唇齿相依。晏婴则不然,他是齐国的异姓大夫,与齐国公室之情感,当然比不上子产与叔向对郑国、对晋国,这使得晏婴虽然重视礼,可以定家国却又无法贯彻。
上有齐景公这样的昏君,下面又是民生困苦的黎民百姓,又屡屡面对“不用则去”这样的困境,晏婴虽然力行礼治,却发现不能完全依赖礼来规范、约束整个国家。因此,他借用管仲法治的观点,如此一来,虽然使得礼得以顺利推动,然而礼却沾染了法的强势性,不再温厚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,这何尝不是造成了礼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本质,终导致礼制崩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