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尔从《军休之友》上读到军旅诗人喻晓谈写军旅诗的文章,特推荐给大家一读。那几年,我俩都坐总政西线班车上班。在班车上,他多次向我约稿,鼓励我多写一点散文,《太阳鸟》一文就是在他的催促下写成的,投稿几天后就上军报了。
——李武斌

军旅诗的写作底色是“热血”
喻晓
作为一个爱好写作的军人,我与军旅诗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,抒写军旅,讴歌军人,成为我崇高的使命。1965年,我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《给一位越南母亲》。那是越南战争期间,我面对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平民,面对鲜血,面对邪恶,以诗的方式,发出的一声怒吼。我从第一首诗起,就感觉到了自己血液的温度。我后来写了很多军旅诗,大都是在激情澎湃、血液债张的时候写的。我意识到,没有热血,对家国天下毫不关心,对强敌威胁无动于衷的人,不能写军旅诗,至少写不出好的军旅诗。军旅诗,应该是枪尖上的灵感,铁马冰河的足音,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,豪迈勇毅,黄钟大吕,为人民军队夺取胜利擂鼓助威。
在我的眼里,“界桩不是圣诞树/铁丝网不是花边……一条边境线/连着英雄铜像/纪念丰碑/诗歌琴弦!”(《边境线》)我凭吊古迹,回望历史,心潮澎湃,发出不同于一般游客的感慨:“古炮不是洞箫……坟墓不是古董/铁舰如山/和平鸽与风信旗齐飞/潮声中军歌浩荡/港湾/碗泊着风云和警句”(《旅顺之思》)。
一位火箭军某基地司令,大半生在深山里为导弹筑窝。退休时,他什么也没有带走,只在洞库里选捡一块石头作为纪念。我为这位老红军战士的故事动容,写道:“对于他石头/代表雄健/代表强固/几十年厮守深山/为导弹筑窝/一腔热血/凝成这伟岸风骨/……一块普通的石头/默默地/证明一个老兵的情愫”(《石魂》)。
1985年,我随一位海军首长远赴西沙,在中建岛种下了一棵椰子树,我培上了半袋从大陆带来的黄土,也把生命种在了岛上,并把诗句献给驻守在这里的天涯哨兵:“相信根须/能从沙砾里获取生存的元素/相信叶脉/能在萧索中弹响豪壮的音符/烈日晒不蔫勃勃生机/风暴抽不碎一身傲骨/为了神圣的使命/它毅然留驻/纵然结出的果实/全是孤独”《植椰》)。我借助椰子树,用诗句诠释生命,那是在长天大海站立的顽强生命。
我曾探访天山南北。我的笔墨触及过云天高处的喀喇昆仑:“乘白云而去/驾罡风而回/胸前背后/都是壮美江山/年轻的战士/有生命的界碑/神仙湾/标示军人灵魂的高度”(《仰望神仙湾》)。
我体验过北湾蚊子的厉害,那是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出国门前的一处洼地,号称“蚊虫王国”。炎热夏夜,边关斜月,包裹严实,浑身铠甲,和蚊虫作战的战士形若外星人。我看着他们巡逻归来,长靴里倒出的半盆汗水,不禁无限感叹:“汗水汗水汗水/生命投进汗水里/一次又一次/反复淬炼锻造/成为无敌锋刃和钢铁堡垒/汗水的成分是信念和意志/是边防军人的坚忍和奉献/真想这汗水能流进课本/成为教材成为营养/培育出新一代卫国的栋梁”(《北湾的蚊战》)。
我曾行走青藏线。世界屋脊,大美河山。空间的转换,独特的生命体验,对于军人来说,我的感受是“一脚踩着太阳/一脚踩着月亮”,日月山,如同高原的第一个台阶。在这里,所有的文字都会伴有军旅的苍凉之美,“一切生存的法则需要重写/日月是沉重的韵脚/一首苍凉的古诗”(《日月山》)。唐古拉山口,一组雕像巍然屹立,我路过,在白云边留下诗句:“我的祖国/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军人/也总是把最高的荣誉授予军人/无数热血沸腾的生命/凝成了这崇高的雕像/这是一棵常绿的树/扎根在整个青藏高原……/他们站在这里/站成了永恒的碑”(《唐古拉雕像》)。
平时,我可能写的是一座山,一个人,一棵树,一朵云,但我的诗的背景必定是整个人民军队,必定有他们的身影和灵魂,也必定只有雄壮军旅才有的博大胸襟和铿锵气韵。在西藏山南的无人区,我邂逅了一个湖,一个岸边只住着军人的湖。此时,我的歌声虽然有些苍凉、苦涩,但仍凸现军人本色,不乏几分豪壮:“雪山把它当镜子/白云把它当浴盆/苍鹰把它当舞池/风是常年的乐队/总在岸边吹吹唱唱/没有名字/亘古冷寂的高原/还未来得及为它命名/如今人们只有说起一个连队/和连队里生龙活虎的战士时/才用极其尊崇的口吻说起它/它是一个捧着军徽的湖”(《捧着军徽的湖》)。
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是军旅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1995年,我参加了重走长征路的团队。江西瑞金叶坪有一棵老樟树,历经雷击火烧,仍铁干虬枝,苍然而立。我像阅读革命家谱一样阅读这棵树:“一棵不死的树/坚强的生命/沉郁而质朴/浓绿的叶子上/悬挂着红色的历史……/一面永远鲜嫩的旗帜/它坚韧的根/连着深厚的土地”(《老樟树》)。
兴国县革命烈士英名碑上有名有姓的烈士有23179名。我数着那些远去的星辰,眼睛湿润了:“二万五千里/几乎每一里就倒下/一名兴国籍战士/他们排列着/像枕木一样/托起共和国的列车”(《英名碑》)。我走过红军第一渡,“瞻望历史的背影”;走过娄山关,“且将英雄豪气,写我新词一阕”;走过彝海,长思“将军和酋长都已远去,唯有故事依然常青”;走过泸定桥,“抚摸着铁索,像一根长长的电话线,通向历史和心灵深处”;走到吴起镇,回眸“苍凉的陕北,演出了一幕震古烁今的戏剧”。我在历史黑色的背景上寻找创世纪式的演练,寻找一部史诗的开篇,寻找壮丽神奇的风景。今年2月21日,我收到长征副刊郑茂琦编辑的微信,约我写一首有关强军的诗。
我一生军旅,军旅诗是我精神的寓所。军旅是青春的方阵,是热血沸腾的年华。军旅诗自然应有浓郁的青春气息。不管你年龄多大,创作军旅诗时,你的心境一定要年轻,要有强健的精神,坚定的意志,恢宏的想象,文字充满锐气和锋芒。我虽已年过八十,白发萧萧,但在创作军旅诗时,觉得自己依然年轻,壮心犹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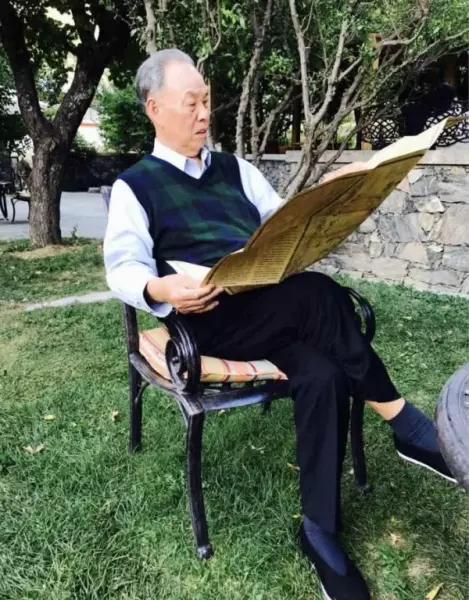
喻晓简介:原名喻元吉,字海涵。湖南娄底人。196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兵第二技术专科学校地下工程专业。历任工程兵某部技术员,师政治部新闻干事,《工程兵报》编辑、文艺副刊科副科长,《解放军报》文化部编辑组长、副主编,高级编辑,大校军衔。中国诗歌学会理事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。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诗集《台胞的心声》、《青春与海》、《翠绿的星》、《灵之烛》、《喻晓诗选》、《红星闪耀》(合集),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原逐鹿》,散文集《最后的伊甸园》,诗歌《朱德的扁担》、《牵牛花情思》等。其作品曾获1964年工程兵文艺创作奖。